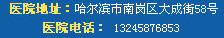一个纯粹的人,就这么走了,但他的精神之光,永远不熄,如同他捐出的眼角膜光明不灭。
作为一名大学教授,他不教课,选择徒步进大山,穿坏17双草鞋。经历过山洪、火灾,跌落过悬崖命悬一线。
为省钱,雨林山洞是他的地铺,布衣是他的棉被,一天只吃一顿饭,饿得没办法了,猪食也吃。
他做这一切,都只是为了魔芋。
他叫何家庆。
01
年2月的一个清晨,何家庆给妻子和女儿留下这封信后,揣着攒了10多年的块钱,一封学校介绍信和一张刊登国家“八七”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的光明日报,孤身一人起程。
这之后,何家庆就“失踪”了天。
何家庆给女儿的信中写到:
何禾吾儿,当你读到这封信时,我已经离开家了,带了一只不太听得见清晰的耳朵和病痛离开了你和妈妈,此次之行,我思索良久,准备十余年,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、大别山区更糟糕,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,倘若不幸,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。
天的西南之行是饥寒交迫、血与泪、生与死交织而成。人迹罕至的西南山区到处暗藏杀机。
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和桂北山村里,他两次夜宿山洞,被毒蛇咬伤,腿肿得发亮,20多天抬不起来,还好自己懂中草药才挽回一命。
在广西百色穿越树林时,与一群硕大的飞鼠搏斗,飞鼠疯狂啄咬他的身躯。
深山老林,饥饿难当,他曾讨过猪食,吃过发霉长了虫子的饼子。身上钱花光了,靠乞讨为生熬过两个月。
死神几次与他擦肩而过,乘坐的中巴车被洪水困住,从车窗爬出不到10分钟,汽车被洪水冲走,车上27人全部遇难。他遭遇车祸17次,大难不死。
扶贫的路并不平坦,热情者有之,冷淡的也不少。人为的伤害并不比自然灾害轻。
02
“你要干什么?”那官员翻翻眼打量伺家庆。
“扶贫。”何家庆赔着笑脸。
“扶贫!关你什么事!”官员冷冷地低下头仍然去看他的报纸。
他不恼,但气偾。这样不关心百姓疾苦的人,如何能改变山区的落后状况。他知道那些种魔芋的芋农们等着他,需要他。
令何家庆欣慰的是,真正的山区芋农把他当亲人、当救星,称他是“农民的教授”。
五里乡站长一把拉着他的手说:“你真是及时雨。”
也许是山区的百姓太需要了解这样的技术知识了,他们总是听到很晚都不愿意离开,何家庆经常从白天讲到深夜,最长的一次连续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。
他甚至永远忘不了重庆市酉阳县青华乡乡亲们。
劳累过度的何家庆发高烧,农民陈远长杀了自家唯一一只老母鸡煨汤给他补身体。烧退后,何家庆执意要走,老奶奶把孙子拉过来对何家庆说:“好人啊,你对山里人有大恩,让孩子给你磕个头吧。”
人群中许多人在哭泣。看何家庆身体太弱了,几名大汉硬是把他抬、背送出40里地。
何家庆把接纳他的各地介绍信粘贴在一起,足足超出5米,那里浓缩了他的西南足迹。
12月28日,带着浑身伤病的何家庆回到合肥,此时的他体重只剩40公斤。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回到家,直到晚上才回家,他像散了架,一睡就是个把月。
天里,何家庆跑遍了8个省区个村寨,3万多公里路途中靠双腿走了多公里,沿途传授魔芋栽培、病虫害防治技术,办培训班次,受训人数逾2万人。同时指导了57家魔芋加工企业。
“魔芋大王”的称号自此响遍全国。是什么支撑他孤身一人闯荡大西南?
再往前追溯,年,命运给了他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——到溪县挂职,任科技副县长。这才让他结识了魔芋。
03
年6月,何家庆到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。
对当县官,何家庆明白,县长过去是“知县”,知县就是知县情。
挂职3年,他骑自行车或步行,天天忙着爬山头钻树丛,公里,跑遍了23个乡,到过所有的山头,采植物标本件。他被百姓形容为“跑山县长”。
元旦前,他写出了15万字的《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》一书,破天荒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展览。
县民们顿悟了,穷山原来并不穷,只缘身在宝中不识宝。老百姓说何县长办了件大好事,把家底摸清了。
“跑山县长”自费购买魔芋种,在绩溪31个地方试种多亩。丰收时节,芋农平均收益元。
自此,百姓对他的称呼也从“跑山县长”更名“魔芋县长”。
百姓的疾苦时刻挂在何家庆的心头,年绩溪遭洪水灾,他冒着生命危险,顶狂风暴雨,四处奔波指导救灾,几次晕倒在洪水中,一个月水中行走,使他染上了血吸虫病,终生未能治愈。
在水灾严重的荆州乡松烟塘村,他捐出刚报销元差旅费,他在留言中写道:“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,我有一份责任,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,却有一颗火热的心。”
04
童年贫穷的生活,磨炼了何家庆顽强的意志。
一家人靠父亲拉板车挣钱度日。何家庆选择到农村去插队,当农民,直到年被调到安庆医药公司,迎着上大学的风潮,又把他推到安徽大学生物系去学习。
在安大,图书馆是他唯一有兴趣呆下去的地方。每天总是第一个进馆,最后一个出馆。
他并不满足书本上的知识,他想到大别山去,到实践中去认识、发现和掌握活生生的植物形态,揭开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奥秘。
年法国传教士F·Courtoris曾到过大别山白马寨采集了号标本。此后,虽有人考察,但都只涉足局部地区。
何家庆为考察大别山默默地准备着,尤其是上万元的资金,对月收入几十元的教师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他省吃俭用,一分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。结婚是人生大事,他也只是凑合一下,六七年下来才攒了多元。
80岁高龄的父亲知道了儿子的心愿,不顾年迈,从安庆赶到合肥雪中送炭。
打开父亲的包,何家庆惊呆了,0元钱是一大堆10元、5元、2角、1角的票子,显然是老父亲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与钱在一起的还有烟盒上的帐单,上面记着何家庆上学期间国家、老师、同学的资助。
在帐单的后面,父亲写道:“读共产党的书,拿共产党的钱,好好学习,努力向上,以求深造,成长后要成顶天立地之业,才对得起党,对得起人民。”
老父的教诲,倾其全部积蓄帮儿子做一件大事,何家庆铭记在心。
05
年3月20日,何家庆走上考察大别山之路。
从年3月到11月,何家庆从大别山最南沿出发,历经3省19县,行程里,沿着山脉采集、观察、实地搜集资料、记录沿途采访,前后共天。
途中的艰难困苦,是坐办公室的人难以想象。阴雨连绵,劈雷闪电,悬崖洪水,野狼出没,都与性命攸关。
水沼里的蚂蝗,草丛里的“皮虱”,也埋设着一道道“陷阱”。暑热、风寒、饥饿、疾病,天,随时可以让何家庆倒毙在大别山的荒山野岭。
一次,何家庆攀登层峦叠嶂的大别山主峰,中途一滑,衣服划破,膝盖磨烂,他一下跪在悬崖上,上下无力,两只手紧紧抠住石缝,求生的欲望使他大叫救命。危急关头,一位猎人冒生命危险解救了他。
他在桐山考察,晚上落住在农民的牛棚里,户农发现了他,硬是把他请回家住,知他有学问,是大学老师,求教不停。
从大别山回来,何家庆的性格变了,变得更内向、更沉默了。妻子以为他在山里呆得太久,与人沟通少,变孤僻了。慢慢才感到,何家庆对生活的欲望比以前更淡然了。
何家庆总是穿着一件外衣,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足矣。常挂在嘴上一句话“该知足了,看看山里的穷苦农民怎么生活,我们这是在天上过日子。”
天的大别山生活,山区人民的真诚与困苦,像刀子刻在何家庆心里,让他难以摆脱。
在他就要摔到山崖下粉身碎骨的时刻,山林里的猎户援之以手;当他生病偷偷住进山民的牛棚时,是山民扶他躺在床上,端汤递水。
这个经得住大自然霜刀雨剑的硬汉子,在这些父老乡亲的真情与苦难面前,却心软得像个孩子。
06
爷爷拉黄包车,父亲拉板车,弟弟妹妹拣破烂。何家庆,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。
何家庆的家住在安徽大学教师宿舍楼里,这个60多平的老房子里,家具只有简单的几件,都是三四十年前购置的,在卧室的门背后,挂着两件崭新的衣服,这是十几年前妻子给他买的,但他却一次也没有穿过。
夜里,他能闻见那草木的清香;清晨,一睁眼似乎能看见那些草木摇曳。
后来,系里另给了房子,标本被转移出去那一天,何家庆在雨里失魂落魄,痛哭许久。
如今,居住条件成了两室一厅。女儿要考大学,独占一室,妻子为了不干扰丈夫工作和休息,便把客厅做卧室。
厨房的碗柜改制成书柜。因为何家庆的父亲留下的遗物唯一可以装饰那柜子的,是一排扭扭捏捏的牙膏盒钉在门腰上,里边分门别类的插着一些写字、画图的圆珠笔和钢笔。
供何家庆著书、备课的一张漆色斑剥的三屉桌,摆在阳台上,桌子上是书稿和教案。很显眼的一个纸盒里,杂陈着一把铅笔头,长的不过三、五公分。这是女儿做作业用剩的,何家庆拿来再用,手捏不住,就插在一枚子弹壳里继续写。
一切,都透露着一种与这个繁荣与奢华时代的距离。
如果说,知识可以转成财富,这段距离在何家庆身边可以说是很短的。
他尽可以到处去讲魔芋的栽培、加工,事实上,有许多地方请他去讲,聘他当顾问,何家庆从来分文不取。同样的,在安徽大学,有这样一位教师下海帮农民栽种葡萄。
何家庆真傻,有人这样说。
07
贫困中的贫困,底层里的底层。
何家庆打小就认识了饥饿和屈辱,也认识了同情和帮助。除工资之外,也时有额外收入,每一笔都写在一个绿皮笔记本上。
那账本里还有一些折合账:
“年9月13日潜山县园艺果酒厂送来板栗5斤,按市场价合10元。”
“年2月28日校科研处发搪瓷烧锅大小各一,价约20元。”
有人曾问过何家庆几个问题。
“你去商场看过那些时尚的商品吗?”
“没有。”他回答得很坦然。
“你记得住你那一万多件植物标本吗?”
“当然,”他回答说,“不只是记得住名字、特点、性能,还能画出他们各自的形态。”
对自己抠门却又十分大方的倔老头,他把工资、稿费、奖金全部攒了下来,花在了一次次的自费调研和考察中。
年、年,他还向春蕾计划捐赠了20万元,资助贫困女童读书。
我羡慕他是个最富有的人。他的精神是超值的财富。
人们总以不解或嘲弄的口气看着何家庆穿着一件年做的中山装上衣。
黑色卡其布已水洗日晒变成淡灰,他依然不肯脱下扔掉,没有人知道那其中的秘密。
那一年,父亲拉着板车上坡时,车太重,脚下一滑,摔倒了,沉重的车辕压断了老人的四根手指。他咬着牙,爬起来,把车拉到目的地。
何家庆报以一笑,“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,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。我哪能为迎合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了我心里面的东西。”
几十年来,这件衣服里珍藏着一份宝贵的情感和一个做人的道理。
年至年,何家庆头顶桂冠身置花丛。他共获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、“全国十大扶贫状元”等证书11个:被评为教授;
拥有了“魔芋研究开发中心”和科研资金65万元。省教委给他奖金5万元。
何家庆一夜翻身,“怪人”何家庆成为“名人”。有记者问他“是怎样的激情使你坚持这么多年?”
何家庆答:“不是激情是感情。激情是短暂的,感情是长期的。”
何家庆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,已经无法进食,只能用汤勺喝水,打营养针维持生命。即使这样,他还是躺在病床上尽力写调研报告。
这是何教授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段视频(画面),也是他给贫困山区留下的最后一份礼物。
这,或许是朴素到极致的“学痴”教授何家庆留给世间最后的光明。
在知识精英、各色大牌资本家云集各种“峰会”的喧嚣中,何家庆却怀揣着一颗火种,寂寥和执拗地走向农民兄弟望眼欲穿的地方—在贫困的西南山区亲手扶贫。
何家庆就像一个先行的殉难者、一个苦行僧、一个无畏的骑士、一个浪漫的歌手。在努力接近何家庆的世界的同时,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自身或者说是普通人与他的巨大精神差距。
何家庆生前说:尽管我很累,但是我精神上是愉快的,希望我所做的这个事情,能够引发更多的人来关心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,有更多的人关心贫困山区的经济发展。
一个纯粹的人,就这么走了,但他的精神之光,永远不熄,如同他捐出的眼角膜光明不灭。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zl/2959.html